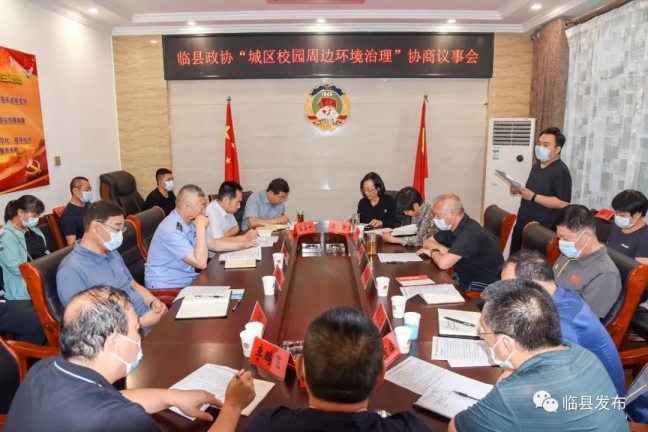童年趣事,捉泥鳅

自古到今,泥鳅一直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家肴,营养丰富,故有动物“人参”之称。我的童年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新,百姓餐桌上荤菜少之又少。泥鳅成了家家户户的“当家菜”。童年的我成了捉鳅大军中的一员。
春季“田间闸鳅”
“闸鳅”就是把田间排水沟用竹制畚箕分段拦住,用脚搅动沟中水,把泥鳅驱赶到畚箕里然后捕捉。这一捉鳅方法代代相传叫“闸鳅”。那时农田冬季一般不种三麦、油菜,都种植紫红英(一种肥田的草本植物),为了使紫红英正常生长,田间每隔2~3米阔开一条竖直的排水沟。两头开横沟把竖沟串连起来排水。农时“谷雨”过后雨水增多,冬眠的泥鳅出洞,水深10多公分的纵横水沟成了泥鳅的游泳池、也成了它们寻找配偶繁衍后代的温床。黎明过后朝霞满天时泥鳅成群结队出来戏水、交配,有时十几条鳅扭成一团,这时是我捉鳅的黄金时机。提着竹制的小畚箕闸了这边又闸那边。用脚搅动沟中水发出“嘭嘭嘭”的声音,小沟中飘起了小浪花,受惊的泥鳅直往前窜,这正中了我的下怀,把鳅赶到畚箕里提起来就捉住了。一个早晨捉2~3斤不在话下,有时初春的寒冷把双脚冻得发紫,可一见到捉到的泥鳅,冰冷的脚不感到疼痛了。但家中大人们看见我的脚冻得发紫,都心疼极了。
盛夏“田角摸鳅”
夏至过后,天气一天比一天热,生长在稻田里的泥鳅和稻苗同步生长,新一代的泥鳅进入生长旺盛期。盛夏骄阳似火,把田间水晒得滚烫滚烫,可怜的泥鳅栖身难,长方形大田的四只角一般比中央的田低,水较深,加上水深处往往有“浮草”浮在水面上挡住阳光,水温较凉成了泥鳅的“避难所”,这就成了我摸鳅的好地方。只要天气有利(天晴高温),披上披肩(一块较大的布遮住后背),下午一到两点钟天最热时去田角摸鳅,有时有的田角一脚踩下去受惊的几十条泥鳅“砰!砰!砰!”的跳起来,它们越跳,我越开心:心想今天我又丰收了!有时候风把披肩吹偏了影响我摸鳅,我干脆把披肩放在一边,这时强烈的阳光直晒在我背上。下午三、四点钟,拿着丰收的成果满怀喜悦回家,一进家门可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吓坏了。我的后背上都是蚕豆大的水泡,他们心疼地说:“宝啊,下次别去了。用你满身水泡换来的鳅我们咽不下去的。”当天晚上睡觉,我痛得哇哇直叫。但为了一家享受美味,第二天我瞒着大人照去不误。二、三天后水泡一个个破掉,后背上一层皮全部脱落,长出来的新皮可厉害了,35度以上高温也晒不出水泡来了,就是太阳越晒皮越黑。就这样,一个夏天餐桌上的荤菜就靠我从田角里去摸出来,既补充营养,又美味可口。
秋冬“寻草掘鳅”
农历十月后田间停止灌水,泥鳅也开始谋划进洞过冬了。当稻谷收割后,有空余时间的人们仍不忘记捉鳅,怎么捉法?叫做“寻草掘鳅”。泥鳅进洞后,它身上的粘液和排泄物肥了洞口的草,这草与周围草不同长得又粗又黑,人们称它为“鳅草”。只要找到“鳅草”一铲下去必是个鳅洞,再往下二铲、三铲,鳅就到手了。这个捉鳅方法虽比前两种方法费时费力,但身上储足营养准备冬眠的鳅更肥、更美味可口、更值钱。有时泥鳅捉得多了吃不完怎么办?爷爷拿到镇上去卖掉换些油盐酱醋回来。有时候腌了后晒鳅干,到冬天吃又香又鲜,又是一道特色农家菜。
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,农田耕作制度变化,由原来的一年种一熟改为一年种三熟,粮食多了,而泥鳅的栖息地破坏了,加上化肥农药的广泛应用,曾为人们的餐桌作出贡献的泥鳅不见了,一度曾消声灭迹。可是聪明的人们没有忘记它,学会了人工饲养,最近几年“动物人参”一一泥鳅又回来了,它甚至被端上了星级餐馆的餐桌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