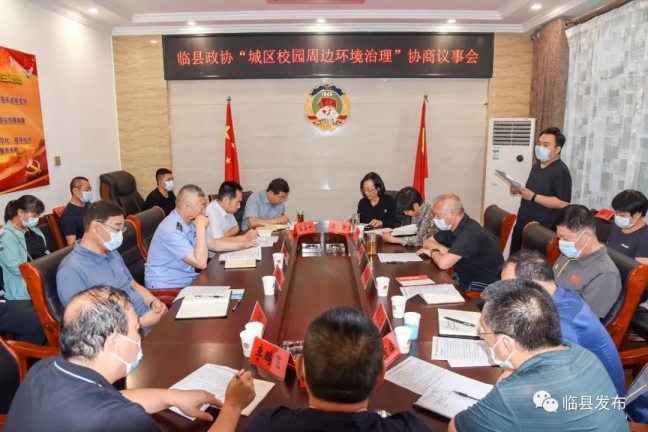城市内涝岂能变成持续性牙疼
城市的价值之一,是为了“让生活更美好”。倘若一雨成灾、门口看海、出行受阻、财产泡汤,甚至还有生命之虞,何谈美好?
城市内涝似乎变成持续性牙疼。近年来,城市内涝的频率大有节节攀升之势。水利部《中国水旱灾害统计公报》的数据显示,2006年至2017年,我国平均每年有157座县级以上城市进水受淹或发生内涝。其中,2008年至2010年这3年间,我国约有62%的城市发生过暴雨内涝灾害,其中暴雨内涝灾害发生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,57个城市的最长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。
何以至此?气候原因首当其冲。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,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多发频发,强降雨有增多增强态势,小时雨量屡屡接近或突破极值。随着城市群的发展、城市数量的增加、城市范围的扩大及城市“热岛效应”的加剧,城市遭受强降雨袭击的频次显著增多。
小范围、短历时、高强度的集中暴雨预测预报难度大、预见期短、精度不高,确实给城市防洪排涝带来很大挑战。
更不容忽视的是城市自身脆弱性。如专家所言,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,表现出人口、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不同要素、结构、层次、功能交织的关系复杂性和形式多样性。在各种资源要素高度密集在城市、城市架构愈加精巧化的同时,城市脱离并悖逆自然的倾向性加大,由城市自身增长所导致的内在风险因素也与日俱增。
这种脱离或悖逆,身居其中的人们多有直观验证。随着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张,湖塘洼淀一个个消失,河道改直瘦身,湖泊萎缩,土地大面积硬化,排蓄吐纳的功能每况愈下。不通则痛,人与自然的命数都是如此。
城市的“郁结气滞”,说到底是人的操弄。人走得太快,灵魂往往跟不上脚步。有人嘴上不说,心里却笃定,包括内涝在内的种种城市病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代价,这恰恰是某些决策者规避其应尽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借口。于是,在“先干了再说”“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去解决”之类思维牵引下,经济开发区与新型城区地势低洼、易涝易灾的先天不足,可以等闲视之;“重地上轻地下”、要“面子”不要“里子”的功利性选择,屡见不鲜。
老城区旧疾难除,新城区又添新患。如果说存量、增量问题的缠绕、叠加、衍生之后,解决难度极大,绝不可能一蹴而就,那么“避险为要”必须谨记于心、践之于行。
事实又是怎样呢?虽然大部分城市编制了防洪排涝应急预案,但普遍存在预案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、演练不充分等问题,缺乏极端暴雨洪涝的应对措施。易受淹的地下空间、下凹式立交、涵洞隧道、地铁、在建工地、易积水小区、棚户区等风险点缺乏必要的警示标记和宣传指引,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、整改不到位;对城市居民的防灾、避险、自救、互救培训用心用力不够,导致关键时刻手足无措……
屡屡发生的城市内涝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一次又一次沉重代价,哀之更要鉴之。城市硬件的脱胎换骨不可能一蹴而就,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通过规划理论、治理理念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的革新来寻找。治疗这种持续性牙疼,需要坚持统筹思维、系统方法,处理好防洪与排涝、工程与非工程措施、统一指挥与部门联动的关系,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,从规划建设、运行管理、应急处置、全民应急素质提升等方面综合施策,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。